陈明昊X马寅对谈:在戏剧节,比戏更重要的就是过节

阿那亚戏剧节源自一个梦想,在海边,做一个开放的、新鲜的、与戏剧有关的节日。
从2021开始,每年的6月,阿那亚戏剧节在11天的时间里,以一种戏剧的方式,将人们包裹在海边戏剧小镇的独特氛围里,生活的戏剧性被放大,各式各样的奇遇自然地发生。
今年阿那亚戏剧节将于6月20日开幕,艺术总监陈明昊和戏剧节主席马寅在海边做了一次对谈。戏剧以什么方式影响着我们?为什么要做阿那亚戏剧节?来戏剧节到底要怎么玩?
如此多关于戏剧的讨论,让我们看到,戏剧是一种生活态度,戏剧节更是正在上演的生活,它不是千篇一律的场合,提供的是新鲜好玩的未知,由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共同创造,永远出人意料,正在发生。

为什么需要戏剧?
认同现场的“危险”,便会迷恋于这种不确定
马寅:听说你刚演出完《暗恋桃花源》,这部戏你演了也有十几年了吧,你现在为什么还会拿出这么多时间精力分给话剧舞台?
陈明昊:如果有话剧演出,一定是优先安排演出,但这几年我基本上半年都投入到阿那亚戏剧节了,别的工作都不安排,时间允许的话中间安排一些演出,今年只演了《两只狗的生活意见》和《暗恋桃花源》,其他的只能等到7月份戏剧节结束了。
我还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,有很多东西要表达,那种欲望,那种欲求或者说你在跟谁说什么,这些形成了表演的现场,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事。其实现在只要演出,就是在表演的状态里边,每一场面对的人都不一样,在不同的状态里获得一些新的思考。

马寅:我觉得这是戏剧有魅力的地方,现场总有不确定,比如当年你在乌镇演《茶馆》,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中场休息时候又出来了,也不知道要说什么,磕磕巴巴的,好像是即兴的又像是带着台词,那种即兴的时刻我觉得是演出最精彩的。
我现在就特喜欢即兴,比如咱们这种聊天对话,或者有人找我做访谈,我任何时候都不想要采访提纲,我喜欢这个问题是新的,现场出来的,我想要即刻的反应和条件反射一样出来的思考,哪怕并不完善,但过程中总会有新的想法迸发出来,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会受益。只要提前给我提纲,我就觉得被一个框架给框住了,就不知道要怎么说话了,而且我自己说过的东西再让我重复,我也觉得讲得挺没劲的,还不如变成大家问我问题,我随时解答。

所以前一阵说你演出的时候“忘词”,我特别能理解你的状态,你需要在舞台上有即兴的东西,也不知道这场会想表达什么,就在现场的状态当中就这么表达了,我喜欢这样的冒险。
陈明昊:按说做一件事应该完全地投入,但是现在也挺神奇的,在台上有时候会灵魂出窍,会思考,突然间就有一个第二自我开始审视第一自我,你说是事故它也是故事。
表演好像就发生在自己完成这种对话的过程中,不完全是去完成一个既定的东西,但这件事又不是刻意的,你一开始可能不是追求这种即兴或者说是突发的东西,当你看到了它跟你的关系,和它带来的那种危险感、兴奋感,别人感受不到的东西,可能它就成立了。舞台其实是很危险的,但你认同这种危险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

马寅:2007年我在长安街先锋剧场看《两只狗的生活意见》的首演,那部戏我看了有一二十遍。当时觉得太牛了,那种对生活的慌张,保安、乐队住地下室那些梗,特别能在当时那个时代环境下让人共鸣,我在现场哭得一塌糊涂。
后来我看《艳遇》和《琥珀》,你在里面虽然都是配角,但我觉得戏都被你抢走了,看戏的时候就总想等你出来,就那种真诚、幽默感,很多出人意料的东西让我特别难忘。
陈明昊:你说的都是我的戏剧青春,一下子回到了青春的时候。还是生活厉害,因为当时不管是生活还是演出都是未知,能演多少场,观众喜不喜欢,都不知道,你必须得跟观众强硬地进行交流,尽情地表达,把自己给撕开了。

马寅:现在再看《两只狗的生活意见》跟那个年代都完全两个概念了,现在看只能叫致敬经典,它已经没有环境带来的时效性了。一部戏要表达的东西离生活很远的时候,靠什么去击中当下的观众呢?

陈明昊:同一个故事内核,有很多种空间内的戏剧表达方式,最重要的还是人跟人之间,在一个特定空间里的一种表达,这种表达可能不一定会跟每个人联系那么紧密,但是一定会有很真诚的东西击中你,这种表达一直能够持续下去。
我更愿意回归到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去想这些问题,我也是在呼唤这种能量出现,看到自己一个当下真实的状态。但是现在最困难的就是时间,当时是有数不完的时间,就只能做这件事,找到一个对手去碰撞,然后发现其实真正的对手是自己,开始跟自己较劲,就有很多东西挤压出来了。

马寅:我觉得你的戏有一个最大的特点,就是你不愿意进入到一个流程和确定性里去,对于戏剧张力不确定性的追求,大于对程式化表演的理解,很多人觉得戏剧的魅力就在于此,迷恋于这种不确定性。
我认为剧场就是记录这种魅力,哪怕你会反悔,会出错,悲剧感就是一瞬间,只有在现场才能感受到这一瞬间。


后来我看你的戏总是紧张,从《茶馆》到《第七天》、《红色》这几部戏,不像早年看戏是欣赏你怎么抢戏,你的幽默感,后来变成一种紧张感,不知道你下一步会干什么,总怕你说错了,每一场演出,都觉得你是踩着钢丝过来的,但这又变成了最吸引我看这部戏的点,因为每一场都不一样,我又会期待着有什么样的“危险”发生。
陈明昊:戏剧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事,是野生的,是自我的流淌,在剧场,我是要建立一个场,我们的相遇不是谁设定的,我要做的,是去发现一些未知的东西。
我在创作《海边的伽利略Ⅰ+Ⅱ+Ⅲ》过程当中,有这种感受,觉得他不是发明了什么,他是发现了,这东西可能本来就应该在这,被他发现了。我们可能被很多东西挡住了,你不交流,或者陷入到某种程式化,可能就没有打开这部分视野。

戏剧本身是一种生活状态,一个慢生活的方式,要在一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,保持一个长思维的能力,去欣赏在未来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事情。就像以前我们看一个很漫长的电影一样。为什么去年有几部国外的戏大家觉得好,就是因为结构和叙事的能力,到后面的张力,让你会在很长时间回味其中。开始欣赏这些以后,你会发现戏剧背后孕育的那种表达能力和审美价值是会打动你的。
我觉得这跟阿那亚戏剧节一样,你来到这里,看到某个景象,感受到现场的东西,其实底下有很多的暗流涌动,就像大海一样。

为什么做戏剧节?
马寅:过去这几年好像有种趋势特明显,很多文化艺术内容,都像一阵风一样,突然间戏剧就火了,突然间音乐节就火了,电影火一阵,办展火一阵,现在又是演唱会,大家确实都在热爱着文化艺术,但好像都是一阵风似的。
在各种类型的文化艺术内容当中,戏剧节肯定是阿那亚做的最深最透的,也是更有影响力的。我记得几年前咱们探讨为什么要做戏剧节,我现在想跟你探讨,大家来戏剧节,是来看什么的,我也看到有人说,我在哪都能看戏,何必要来戏剧节,可能演的还没平时好。

陈明昊:有一种版本叫戏剧节版本,因为这个戏不管在哪演过,到了戏剧节它就不一样了,就是充满了意外,在阿那亚戏剧节看到的,一定是只有在阿那亚才有的戏,在这一刻、在这里发生的戏剧,是唯一的。
比如我在阿那亚戏剧节的那几部戏,每一场的状态是唯一的,就只能在这儿发生,我只能探索我感受到的东西。它蕴含着人类文明的巨大能量,一个人类生活的社区,存在于大海这种通向无限未知的地方,引发你对于真相的探索欲望,然后形成了戏剧的边界。

大海还是太多能量了,带来的那种感受的丰富性,引发很多创作和表达上的感受。这些戏剧是长在这里,就跟你的身体的一部分一样,离开了这个部分,就失去了活力,再搬回到剧场里去演,原来的东西丢失掉很多。
从整体的角度,戏剧节肯定是一个节日,对演员和观众都是,就是过节的感觉,每一年,在这个时间,带着一个玩的心态,大家要来见面了,你要说我们在这几天集中演戏,这就没意思了。

马寅:其实阿那亚也不是说刻意要做什么节,大家都喜欢过节,春节、端午、中秋节,无论是戏剧节也好,还是音乐节、电影节,它固定在某一个时间点,就成了这一年当中大家期盼的一个假期。这个假期到来之后,这个阶段就是一个以戏剧为主题的生活方式,不是说非得买张票,看一场戏,你来到这里,就参与到了这种生活当中。
孟导给我讲过一个故事,让我一下子对阿维尼翁戏剧节有了认知,说在大街上一男孩扛一马桶,说着话往地上一放,一个女孩裤子一脱往那一坐,大家都围观,然后就发传单,结果过去买了票进门一看,跟刚才一点关系没有。我这才知道戏剧节是什么,很原始,就是玩,其实就是一个态度。


陈明昊:戏剧节就是各种形态掺杂在一起,带给人一种综合的感受,让来玩的人,感觉到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就行了,不可能说我今天看了一个戏,我会记一辈子。国外的戏剧节,也不是为了来看什么宏大的、经典的戏剧,戏没那么重要,有比戏更重要的,就是过节。
我们去阿维尼翁演《茶馆》,在城外的一个剧场,来了好多年轻人,到中场好多人看一半就走了,我们以为人看不下去了,结果等我们演完出来,在街上他们沿路给我们鼓掌,说你们演的太好了。为什么提前走了,因为到点了该去吃饭喝酒见朋友了,他们觉得你演得特好,但不代表要从头到尾看完,不影响我对你戏的评价,我已经体验到了,感受到了。


马寅:我记得在乌镇戏剧节,我去看你的《茶馆》,那个戏三个小时40来分钟,我中间睡了一个半小时,还有《叶普盖尼·奥涅金》、《三姐妹》,三四个小时的戏,中间我都睡着过,但是我觉得连睡觉的过程都是在看戏,在剧场里睡一觉也是特别好的感觉。因为我进入剧场,就已经在感受了,当下的某种感受带给你了,就够了,别把戏剧当电影看,别把电影当电视剧看,咱们可能有时候还是太严肃了。
有的戏我甚至觉得过程就是折磨你,但那种不舒适也是一种挺好的体验,被折磨完了之后,还挺爽的。每次进到剧场都可能出乎你的意愿,很多地方有不唯美、不舒适感,其实不见得是享受,它不是为了舒适,戏剧没有办法让你舒适,座位本身就不舒适,不会像电影院那样让你坐一个沙发软座上。


陈明昊:这就是戏剧的一部分,破坏舒适性。《海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凌晨3:00演出,熬三个小时看日出,太不舒适了,但这难道不是戏剧节令人难忘的一部分吗?
为那戏我真是站在海边待了三个晚上,等了三天日出,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发生这件事。我其实无非就是比观众早来了一会。每次我到戏剧节,都只是比观众早来了几天,可能心更早到达,然后身体又到达,再等着观众来汇合,最后我们一起散去。
马寅:《海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去年第二次演的时候感觉都跟第一次不一样,第一年后面还是工地,现场还有吊车,本来说没道具结果现场正好有两台巨大的推土机。观众从工地围挡旁边摸着黑进去,不知道往哪走,也不知道要干什么,但是看到日出他就明白了。就是这些真实的东西放在我们面前,比制造一个东西,力量要大多了。

包括候鸟300,一切都是野生的,即兴的,造一个沙城,拿脚手架搭一个美术馆,也不知道会见到什么人,大家能做一个什么东西出来,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不确定和那种荒野之间生长出来的东西。
而且每年的观众都在变化,大家感受的点都不一样,除了戏剧当中那些永恒东西不变之外,每年总得有点新鲜好玩的未知,有更丰富的体验。戏剧节不是一个传统营业场所,不是个千篇一律的场合,不能让大家太熟悉了,这至少是阿那亚应该做到的地方。

陈明昊:哎,我突然觉得,戏剧节应该是什么样的,好像是让大家来思考的问题。我们在思考,观众也在思考,创作者也在思考,所有事情都在发生着变化,戏剧的创作环境和表达空间都是发展的。
阿那亚戏剧节本身就带着一种非常开放的视角,当代的表达,没有一部戏是程式化的表达,跟生活很近,也容易引起争议,《海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》骂的人也很多,我觉得引起争论挺好,任何关于戏剧的争议,都是戏剧的一部分。
阿那亚戏剧节给更多的戏剧工作者,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创作氛围,我做艺术总监,告诉他们的是在这儿不能干嘛,能干嘛的都是你们来了自己去发现的。理性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。你看我好像是在胡作非为,特别感性地由着性子来,其实都是理性在作用。

马寅:你第一届做了《海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》,第二届是《红色》,今年做《海边的伽利略Ⅰ+Ⅱ+Ⅲ》,这次的戏据说还提供三餐。你对这届戏剧节最大的期望是什么,跟前两届相比?
陈明昊: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对话,更多的现场交流。让戏剧起到作用,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奔赴。
我从《海边的伽利略Ⅰ+Ⅱ+Ⅲ》里面得到一个启示,任何对真相的寻求,都是从怀疑开始的,比如对剧场的怀疑,对表演的、技术的,都值得怀疑和讨论。

一说到这我其实有点后悔,应该还在凌晨三点,还是用那样的一个状态,演一个不一样的戏,结尾还是日出,都是看太阳,一个代表爱情,一个代表真理。最讽刺的就是一模一样,因为看日出的确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,但突然间又很美好,你来了、你看到了、你觉得值了。
我对伽利略的一个浅显的理解,就是人家在搞实验,本身我这就是一个实验,吃饭我觉得是比较幸福的一件事,伽利略对我来说就是望远镜,让我看到了更远的未知的东西,我觉得宇宙的未知就像大海,没发现新大陆之前,你认为新大陆是谣言。当你像船一样在海上航行,驶向它的时候,你就会获得寻找真相的快感,看向宇宙就是未知的幸福感。

供图:在野照物所
公众号承办:智璞文华
点亮星标






版权声明
本文仅作者转发或者创作,不代表旺旺头条立场。
如有侵权请联系站长删除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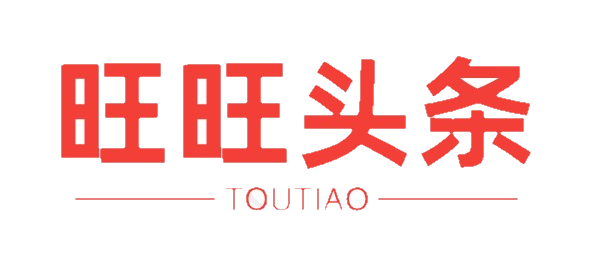 旺旺头条
旺旺头条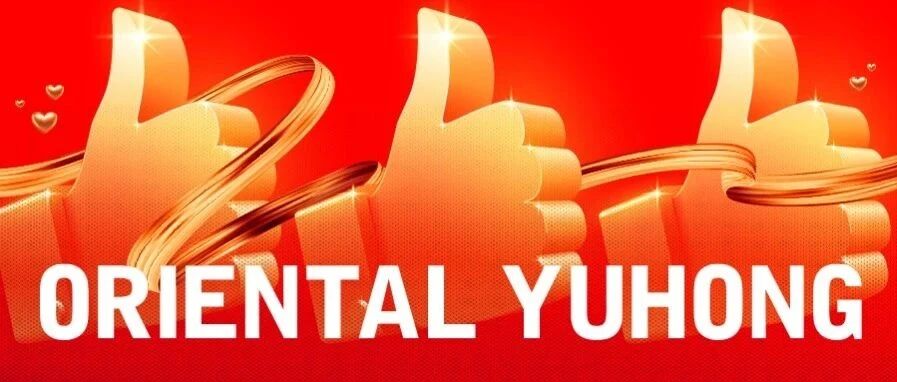




发表评论:
◎欢迎参与讨论,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、交流您的观点。